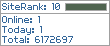何式凝指婚姻不神聖,以一例說明。「我有個學生返大陸研究一個婚禮,台上七情上面,原來男的是 gay,女的是 les,他們不過做場 show。」
非常人語
不能說的秘密 何式凝
何式凝是港大教授,研究性學二十多年,反對婚姻是愛情的唯一出路,她也身體力行,不婚,多年來奉行多邊關係,同時與幾個男人談戀愛。
她一向給人肆意縱情的印象,骨子裡卻是偏執之輩,二十多年來,她執意愛着一位男同志。她沒得佔有,只好練習「不佔有」的愛,把靈慾劈開,廣交善緣。「我一定要諗一種方法,去 justify我去愛一個我不該愛的人。」剛滿五十五歲的何式凝,總結自己的學術與人生。
父親是港英政府特務,她自小懂得保密,她發表了許多性小眾幽秘的慾望故事,自己的事,卻有口難言。
幾年前,她的起心肝離開那同志。像一場出櫃儀式,她開始寫自傳,四年來翻來覆去改了好多遍,過去不能說的,都寫下了。
她現在只有一個親密男友,還想過結婚。
雖然,那男人有老婆。

何式凝把自己對性與愛的看法搬上劇場,五月公演。她露背上陣拍海報,海報上的宣傳句是「學習中出精彩」,可三個字一組讀,也可兩個字一組讀。
記者採訪何式凝那幾天,何式凝也在採訪。對方是日本的女學者,中年,研究日本風俗行業,但何式凝看中的,不是她的學術成就。十幾年前,那女人愛上女人,離開丈夫和一對子女。十多年後,她還愛那個女人,兩人想生孩子,當下在日本找捐精者。
故事重口味,或許有人聽得皺眉,但落在這位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耳中,如福音,叫人自由。「人到中年,還可以選擇過新生活,社會上有這樣一個女人,好多人得到安慰。我請她來,有個已婚女人很想見她,因為她也愛上了女人。」記者可憐日本女人的丈夫,丟了妻子。何式凝卻壓根不信任婚姻。「家庭婚姻,只不過是一種方式,有腳(對象)的話,我都會鼓勵快點結,但我不會把它當作很崇高、神聖不可侵犯。我有個師奶受訪者講得好,佢話『如果你看婚姻是學習,那是很好的經歷,如果看婚姻是結果,你咪賴嘢囉。』」
何式凝研究都市愛慾,八十年代末,當肛交同志還會被判終身監禁,當學院的社會研究還只是老人問題、青年問題時,她已研究同性戀,問同志如何戀愛。近年採訪師奶,像五十八歲才引刀變性的「女人」,領養兒子的獨身女人,為二奶仔做保母的大婆,她喜歡收納社會不容的愛,引學術、理論,把本來不能言及的社會禁忌說得合情合理,在她看來,沒有不該的愛。
「咁多年來,我成套理論,就係要諗一個方法,去愛一個其他人認為你不該愛的人。」那是為人鬆綁,其實也是救贖自己。「因為,我一定要諗一種方法,去 justify我去愛一個我不該愛的人。」
那個不該愛的人,是基佬,而她愛了他二十多年。「如果我在愛情路上,無同一個基佬搞咗咁多年,可能到依家仲活在社會的框裡。」
入櫃
何式凝是藍田聖保祿中學的高才生,虔誠基督徒,年輕時在《突破時刻》當廣播義工,志願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。
何式凝第一次遇到同志,在八八年,她的男性好友自道性向。多年來,這個啟發她做同性戀研究的朋友沒名沒姓,現在大家都知道了,他叫黃耀明。
但她喜歡的,是《突破時刻》另一位男人,他填詞。她與詞人拍拖,無耐懷疑他的性取向,找黃耀明做軍師。「明哥話响淺水灣見過佢同一個鬼佬一齊,但照計唔會,如果係,點解要溝我?」你們倆,沒有那個嗎?「拖吓手,基督徒嘛,所以咪蠢囉。」她自嘲:「依家講番出去都笑爆啦,你同條仔咁多年,無搞過嘢,又唔知佢係基。如果依家識一個男人,三次都唔同你上床,你快走啦。」
在她搞清楚前,那詞人留下一首詩不辭而別,她至今記得清楚,他消失了一年零八個月。一年零八個月後,大年初一,他找回何式凝。「佢話冇咗我,覺得有好大缺欠。」
兩人繼續無性之愛。她七上八落,又找黃耀明問卜。
「如果係,你有乜打算?」黃耀明問。這次她提起勁,說:「就算佢係,我都一樣咁鍾意,愛一個人,有好多方式,我咁愛佢,咪諗一個方式同佢相處。」
「當時好似基督徒決志咁。」她又自嘲。當日黃耀明聽後,戥佢可憐:「我如果係你就唔得,肉體的事,對大家好重要。」
八九六四之後,詞人要跟愛人同志離開香港,臨行前終於向她認了。「他說沒有我不完整,沒有他也不完整。原來他不是想撇我,我仲好開心。」那天起,兩人天各一方。

她穿低胸裝,從徐立之手上接過港大卓越教研工作獎。(《蘋果日報》圖片) 
何式凝訪問了四十個師奶的愛慾情事,研究計劃名為《第二春》,她發現,師奶壓抑。「大家表面好似好尊重你,但師奶都知道,真正社會要的樣貌、事業、地位,她們都沒有。男人可以隨時搵個後生妹,那師奶呢?叫鴨都貴過人,師奶在性方面真的很壓抑。」這天她訪問日本學者,一個中年轉性向的女人。
家嫂
日復一日,何式凝打着每分鐘十六元的長途電話。「我知道好貴,但好似一世人,都無乜令你咁開心。」對方病了,她便乘早機過去看病,有時則倒過來。「我病了,他也會飛過來,我們真的有這樣相愛過。」
詞人另有男友,何式凝自此也有不少男伴,她為了讓幾段感情共生,曾安排四人同枱。「佢條仔對我都唔差,但都有 tension。大家好努力,試過好多方式相處。」每次她那些男友叫她與詞人斷絕來往,她一定說不。「我一開始便說不可以,最後當然 work out唔到。」那詞人有沒有吃你男友的醋?「佢當然無可能去介意,但當然,佢介意。」
何式凝自言仆過很多街,撼過許多牆。「為咗見佢,我可以飛去佢屋企,响佢條仔面前扮係佢朋友,住响佢屋企,夜晚佢哋响隔籬房搞緊嘢,我都係咁,我都唔知點解做得到。」何苦呢?「我一定要去接受,我要有呢種能力,因為我好想見佢。」

黃耀明出櫃當晚,回到後台,問何式凝:「我有沒有失禮人?」何式凝當日研究同性戀議題,就是因為好友黃耀明之故。 
採訪三日,何式凝換了三種風格。頭兩日,每當她見到鏡頭,便整理劉海,到第三日,她索性剪短了才見記者。
廿多年來,何式凝在詞人父母家中過年過節,伯母把她當新抱,有時她以為這家嫂一角,會當一生一世,卻在某些場景瞬間醒來。「我們有講過,如果生個仔都幾好,但他立刻想到用很科學的方法,我就知道,原來佢真係好嫌棄我。」所以你要將靈慾劈開?「無錯,所以後尾發覺,唔得喎,要放自己去試吓各樣嘢,要找回平衡,如果唔係,俾人 reject嘅傷害會令我從十六樓(住所)跳落去。」就是在這種狀況下,她發展出與其他男人的多邊關係。她比喻:「只有廣結善緣,才能有心有力去愛一個人,而不是想佔有。」
何式凝也沒想到,幾年前一次在男家的尋常飯局,讓她徹底退出。當日詞人母親生日,她如常扮演家嫂,詞人的男友卻也到場。「原來係 coming out party,唔該你早啲講聲,我覺得超唔 OK,因為我覺得,我先係家嫂。」一頓飯吃得辛苦,完了伯母着詞人送她回家。「我很想他送我回家,但他只送到去樂富地鐵站,我上了地鐵,一直喊到去金鐘(家)。
「我同自己講,唔好再幻想呢個人為你做乜,佢只可以送到你去地鐵站,只係咁多。
「我雖然坐响佢媽媽側邊廿幾年,但今日响佢旁邊嘅,絕對唔係我。佢媽媽照樣夾餸俾我,照住我,但我見佢同樣夾俾佢條仔,我已經知道,佢媽媽接受了,我的歷史任務已經結束,而我仲以為自己扮緊家嫂。」何式凝再次參加男人的家庭聚會,已是伯母葬禮,那時她已不用再裝。
他一直把你當幌子嗎?「我們確實係有感情,不過都明白,佢想有個女人,响佢身邊,又為佢搞掂屋企。」
Someone like me

父親是殖民政府的特務,每天到某些指定地點蒐集情報,她到過那裡幾次,寫自傳的時候,她問過一些親戚,但都不欲多說。「他連 file都無,唔可以話自己係公務員。」
何式凝離開詞人,研究也從同性戀,轉而探討師奶,在她看來,後者比前者更壓抑。「社會給師奶一個地位,要很 proper,好正經,這已是捆綁,因為要符合別人的期望。但『基』很不同,社會覺得你根本是個壞人,擺明當壞人的,可以豁出去。」
她要自由,不怕當壞人。記者問她,現在有多少男友。她說,有性關係的,只有一個,是在美國長大、日本工作的中國人,有妻兒。兩人早在十多年前認識,那時她在看網上分類廣告找房子。「有個廣告,條友話自己做生意,成日到亞洲,唔想一個人吃喝,想找個伴,但又唔想女人圍繞自己。當時心諗,你係咪咁寸?」她回對方,居然錯用了港大電郵,正當她害怕墮進某些網絡陷阱之際,對方見她在名校司職,回了電郵。
此君與她過去認識的很不一樣。「以前認識那些,是高高瘦瘦 academic樣,這個很薯很老土,件衫攝埋入底褲那種,會對你講: I' ll be there for you。係好娘,但聽落又 OK。」認識的時候,男人還只是平衡詞人的眾多伴侶之一,現在已是唯一,以說起此君時的表情所見,她樂在其中。幾年前,她賣了半山的八百呎住宅,存了一筆錢;只花了百多萬,住進油麻地四百呎的單位,但求輕身上路。她還學起芭蕾舞,完成中年轉身的儀式。
沒有覺得對不起他太太嗎?「無,真係無,又唔係同佢結婚,只不過在他心中有個位置。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他的基本人權同自由。」甘心做第三者?「你真係要放開,睇得咁重要,你人生唔使行。無錯,一般人有嘅幸福,我唔會有,即係唔會有個人來接我走,或者病嘅時候有個人响你身邊,但一般人無嘅幸福,我又有好多。」
但誰說得準確。兩人認識了十幾年,最近首次講起結婚。「我同佢講,第時你離婚,如果娶個𡃁妹,我會頂唔順。」那男人回道:「唔會,再娶的話,都會係 someone like you。」她倒說得直接:「唔好 someone like me得唔得,話 me得唔得。」男人打蛇隨棍上:「吓?乜你有興趣結婚?」
「如果你真係離婚,我會報名同你結婚。」她應道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